广西农耕文化有民族性、自主性、自足性、和谐性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由广西各世居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经过磨合、交融形成的。但在古代,广西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六朝之前一直采用较为原始的火耕水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直到宋朝官方向广西地区派遣或任命官员后,广西各少数民族才逐渐接触并学习了中原农耕技术,也形成了与当地汉族群众相近的农具文化、田间文化与民俗信仰。而近代以来,随着农业生产方式与商业发展出现变革,广西各族群众实现了无竞争、互补型的农业经济格局。这种非排他性经济的发展,也促使广西各族群众在思想上进一步融合。农耕文化是依托于农业生产与农业经济基础产生的风俗文化。广西各民族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基本上都是农耕民族,有大致相似的生计方式、文化特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这种经济联系性极大地减小了各民族之间的隔膜、差异和差距,从而大大增强了广西民族团结的韧性,这也为广西民族团结增添了一副稳定剂。
一 广西农耕文化的整体特点
广西农耕文化是以农民为主体、培植水稻为客体,在长期农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风俗文化。水稻是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种植最广泛的粮食作物,以种植水稻为基础,从水稻生产中衍生出了饮食习惯、丰庆节日等文化习俗。这些文化习俗可以从物质形式与非物质形式中体现出来。比如,依傍水稻而居,为防止湿气与毒蛇伤害而发明了干栏式建筑;为便于田间耕种,而选择以深色、宽松型着装为主;结合水稻的生长习性,有关文化活动都是根据农忙时节来举办的;为满足水稻的生长需求,促进水稻生长,便产生了求雨拜神的节日活动;等等。
广西农耕文化的民族性。广西少数民族在与自然进行抗争的过程中,懂得了如何与自然相处。为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平安幸福,少数民群众将大树、青蛙奉为神灵,比如村边的大树,人们逢年过节给它上香火,祈愿万事如意,一切顺心;人们崇拜与奉祀青蛙,形成各种有关蛙的节日活动,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蛙可以带来幸福,能够保佑他们平安健康。广西少数民族多以种植水稻为主,但不同少数民族所具有的农业文化是不同的,其基本特点与历史传统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比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毛南族主要居住在上南、中南与下南三个地区,主要语言为毛南语,通唱毛南语山歌,拥有共同的传统节日与风俗文化,然而分散居住在其他地区的毛南族,具有自己的语言与风俗习惯,但他们也认可当地民族的传统文化。
广西农耕文化的自主性。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各种村规民约,来约束大家的行为,以维持农业社会的正常运转。这些村规民约包括口头上的道德约束与以文字形式确定下来的条文规定,违反者必然要受到相应的惩罚,或者由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来主持问责,最后再决定处罚方式。少数民族村寨的矛盾纠纷处理通常都采用这种形式。
广西农耕文化的自足性。这是由广西少数民族的居住环境决定的,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偏远地区,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因而村寨居民的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品大多数都是自己制作的。村寨居民常年生活在乡村,物质生活上虽然不富裕,但知足常乐,白天在田间耕作,夜晚村民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以歌抒情,农忙时期村民之间互帮互助,忙完之后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因而少数民族群众在精神上是满足的,邻里和睦,友爱互助,一片和谐。
广西农耕文化的和谐性。广西少数民族是分田到户的,村民们可自由选择劳动的时间、方式以及强度,不受任何制度规则的约束,在精神与行为上都享有绝对的自由,长此以往村寨居民也就形成了休闲、轻松、愉悦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生活清贫,物质匮乏,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自在的生活态度,养儿育女、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便是他们最大的满足,这种生活文化是自由的、人性化的,更是和谐的。
二 从火耕水耨到更先进的生产方式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曾经对楚越之地的农耕情况进行描述: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訾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①]
而岭南也属于楚越之地的一部分,说明当时的楚越之地居住人口稀少,且生产方式都是以火耕水耨为主。产铁技艺传人岭南之前,岭南地区所用铁器都来自中原,铁器数量很少,且未得到广泛使用,生产技术是非常落后的。
东汉之后,生活在岭南一带的越人经过长期的演变发展,形成了乌浒、俚、僚等族群。《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也有记载,灵帝时期,郁林太守谷永是个恩德信义的人,乌浒人信服与崇拜他,遂被他招为麾下:“灵帝建宁三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②]
汉代时期,西瓯与骆越人都集中居住在郁林郡地,后来经过长期的融合发展,形成了乌浒人。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中记载:
交州与广州的边界被人们称为乌浒,而东界位于广州的南边、交州的北边。其中也指出,“理”生活在广州的南边,而苍梧、郁林、合浦、宁浦(今广西横县境)、南凉(今广东恩平市)五郡离中央有千里之远。[③]
从中可以知道,乌浒人、俚人都生活在郁江、得江、西江一带,而这片地区都发现了汉代生产的铁农具与铁犁钟。虽然并不能说明铁犁牛耕广泛运用到乌浒人、俚人的生产生活中,但会对当地火耕水耨的耕种方式产生影响是毫无疑问的。火耕水耨的耕种方式是将田间杂草与蓬蒿用火烧后,把草木灰留在田间,再下种禾苗,待禾苗长高再引水人田,将杂革烂在地里,化作禾苗的肥料,促进禾苗生长。这也给后人实施人工施肥以启示。根据汉墓出土的文物可了解到,东汉时期,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已经学会人工施肥。比如合浦望牛岭东汉墓出土的陶屋为干栏式建筑,人的居所与饲养牲畜之地连在一起,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学会将人畜粪尿用作肥料;梧州市东汉墓出土的陶屋,上层是厕所,连接下层,下层为带有“几”形窦洞的牲畜圈栏,供牲畜进出,这种设计将人畜粪便连在一起,为田间耕作提供更多肥料。[④]
晋朝之后,对岭南土著的称谓逐渐发生了变化,人们称原来的乌浒人为俚、僚或俚僚。《南齐书·州郡志》记载,广州居住有俚、僚之人:“广州,镇南海。滨际海隅,委输交部,虽民户不多,而俚獠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⑤]《南史·夷貊传上·海南诸国》中提到“广州诸山并狸獠,种类繁炽,前后屡为侵暴,历世患之”。[⑥]《隋书·食货志》又记载江南一带的风俗,“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又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其军国所须杂物,随土所出,临时折课市取,乃无恒法定令”。[⑦]从中可知,六朝结束之前,岭南俚僚一带火耕水耨的农耕方式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六朝统治者不断对俚僚人发起战争,而对愿意归顺朝廷的俚人,则将其入户。赋税是随着田地产生而产生的,对俚人集中居住的溪洞,朝廷委派俚帅来进行专门管理,也就是所谓的“以俚治俚”政策,该项政策的实施有利于维护当地社会稳定,为农业生产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高凉郡俚人渠帅(首领)冼氏与高凉郡太守冯宝结为婚姻,至此,封建制度开始在俚人中实施,俚人原有习俗制度遭到动摇。冼氏一共经历了梁、陈、隋三个朝代,其威望在岭南一带维持了60多年,她的儿子冯仆是阳春郡的太守。陈末隋初,为维护高凉地区的稳定,她走访巡视了十多个州,俚、僚首领都归顺于隋朝。
谯国夫人者,高凉冼氏之女也。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夫人幼贤明,多筹略,在父母家,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每劝亲族为善,由是信义结于本乡。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岭表苦之。夫人多所规谏,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梁大同初,罗州刺史冯融闻夫人有志行,为其子高凉太守宝娉以为妻。融本北燕苗裔,初,冯弘之投高丽也,遣融大父业以三百人浮海归宋,因留于新会。自业及融,三世为守牧,他乡羁旅,号令不行。至是,夫人诫约本宗,使从民礼。每共宝参决辞讼,首领有犯法者,虽是亲族,无所舍纵。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
遇侯景反,广州都督萧勃征兵援台。高州刺史李迁仕据大皋口,遣召宝。宝欲往,夫人止之日:“刺史无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诈君共为反耳。”宝日:“何以知之?”夫人日:“‘刺史被召援台,乃称有疾,铸兵聚众,而后唤君。今者若往,必留质,追君兵众。”[⑧]
冼氏和冯氏“从民礼”,劝导俚僚等人归顺朝廷、鼓励汉俚通婚等行为,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交流,促进了各民族和谐发展。
夫人并盛(圣旨)于金箧,并梁、陈赐物各藏于一库。每岁时大会,皆陈于庭,以示子孙,日:“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具存,此忠孝之报也,愿汝皆思念之。”
时番州总管赵讷贪虐,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长史张融上封事,论安抚之宜,并言讷罪状,不可以招怀远人。上遣推讷,得其赃贿,竟致于法。降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上意,谕诸俚獠,所至皆降。[⑨]
唐宋之后,居住在交州与广州地区的人们被编入州县,史书再也没有记载过俚人名称,表明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发展,郁江、得江、西江一带的俚人已经完全和汉人融合在一起,农业耕种生产技术也逐渐汉化。
俚人农耕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从火耕水耨变成了牛耕。《南州异物志》记载,俚人尤其看重水牛,曾经有人用孩子换取水牛。可见,俚人之所以重视水牛,是因为水牛对农田耕作具有重要作用。俚人主要用牛来进行农耕,但也有杀牛祭祀雨神祈求上天的风俗。苏东坡在《书柳子厚牛赋后》一文中说:“岭外俗皆恬杀牛,而海南为甚。客自高化载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风不顺……既至海南,耕者与屠者常相半。”[⑩]海南的俚人从高化买入牛,大部分人都是用来农耕的,这也是火耕水耨转变成牛耕的依据。
三 相似生产方式带来相近的民族意识
1.相似生产方式带来相似的农具文化
直到近代以前,大瑶山都没有任何炼铁工坊,不生产铁,铁器的原材料都是从汉族地区引入的。瑶族包括五个族系,其中只有花篮瑶是具备制造铁器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六巷村村民精通打铁技术,其中就有八户人家具备打铁技艺,而关于该地居民从什么时候开始打造铁器的史实却无从考究。花篮瑶的铁器制造涉及刀、斧、锹、锄等农具,还包
括猎枪,当地打铁仅是在农闲时期进行,或是需要打制与修理农具时才会打铁,并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职业或行业体系。“瑶族打造的铁器,不管是生产工具还是家具,大多数都是从汉族地区输入的,或是雇用汉壮两族的铁匠来帮忙打造。”[11]
瑶族大部分农具都来源于汉壮地区。20世纪30年代,瑶族农具打造技艺依然较为落后。王同惠在深入走访调查大瑶山之后发现:
花篮瑶虽然在铁器制造上有一定的历史,但其铁器制作水平较低,当地没有专门从事打铁技艺的人员,大多数人也仅能制造简单粗糙的竹器和木器,制造竹器的材料是青竹的外层,比如篮筐之类的器具。木器大多是用来储水的,采用整块木板制作而成,除此之外,当地人们还会请汉人来制作桶、椅子等,铁锅等需要到集市上购买……花篮瑶人们可以自己制作些比较简单的生活用具,但大部分都需要借助汉人。[12]
清末到民国这个时期,汉族地区的农具逐渐被广泛应用到瑶族的农田耕作当中,瑶族原有农具被新升级农具所代替。南丹县大瑶寨瑶族学习汉人的经验技艺,从汉族地区购买割禾工具——锯镰。瑶族从三百多年前就开始使用刮铲,这是瑶族使用历史最悠久的工具,但刮铲使用效率不高,用途也仅是刮杂草。光绪年间,瑶族发现汉族都是用重量在二斤以上的大锄和大月刮来挖山刮土,这种铁农具效率极高,尤其是大月刮,形状像半月,刮口呈弧线状,尖角分布在两边,既能铲土又能掘土,用于山地耕作会大大提高其耕种效率。瑶族人民认识到这些铁农具的优点,都愿意引入使用:“三角刮在瑶族耕作中使用较为普遍,其用途主要包括挖土、扒土、培土、中耕、修畦、积肥、种菜等;尖刮的尖口如桃叶状,为铁制工具,运用范围较窄,仅合适用于石子较多的耕地上,不具备铲土功能,用来扒土也不方便。外出务工的瑶民,看到壮族人民使用三角刮来挖土、铲土与扒土,耕作效率较高,便从壮区购买带回瑶族地区进行推广,于是三角刮逐渐代替了尖刮在瑶区的使用。”[1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经过长期的融合发展,瑶族地区所使用的农具与汉族、壮族地区使用的农具基本相同,且如果以家庭为计算标准,瑶族每户家庭拥有的农具数量比汉、壮族还要多。
2.相似农耕方式带来相近的田间文化
壮族的主要农作物是稻谷、玉米等,拥有历史悠久的稻作农业文化。壮族人民依赖稻作农业生存与发展,因而,壮族人民的活动都是围绕稻作进行的,也就产生了以稻作为核心的一系列祭祀文化活动,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在广西东兰县,每到播种时节,人们都会在田坎上插青,以红糯米饭与彩蛋作为祭谷神的祭祀品,并吟诵《播种谣》,完成这些仪式之后才开始把谷种撒到田间,以此来表达祈求与盼望之情。歌谣唱道:
谷种谷种,嫁你下田,红蛋送你身边,红饭送你面前。
你要先吃饱,你要吃得甜,你要争口气,你要绿满田。
青似芭蕉叶,壮似甘蔗秆,铺到山顶,连到天边。[14]
为防止鸟兽毁坏秧苗,壮族人会一边念诵《茅郎歌》,一边将茅草人扎在田地上。歌谣唱道:“茅郎茅郎,你守地中央,眼看六路,耳听八方,哪个不自量,折断它翅膀,剥掉它毛皮,挖掉它心脏。”[15]对于与农作相关的对象,壮族农人都怀有崇拜、尊重之情,并为其举行相关的祭祀礼仪与唱诵赞美的歌谣。壮族将每年的四月初八定为“牛王节”,节日当天,年岁最大的牛会被家长一边唱着歌谣一边牵着绕转桌子,“牛咆我的财咯,四月八来了,脱轭节到了,我把牛来敬,我把牛轭脱,让你喘口气,让你歇歇脚,吃口好料子,听我唱牛歌”。每当唱到这一段,就会喂牛吃一团五色糯米饭和腊肉,之后又继续唱道:“样样经过你肩膀,人们吃早饭午餐,都靠你出力,犁地黄牛犁,耙田水牛干,下雨你也去,刮风你也走,我们永远不忘你的功劳,牛!”[16]这体现了壮族农人对牛的感激、尊敬之情,也表达了壮族人
民祈盼来年丰收的愿望。
唱诵歌谣是因为人们相信可以以真诚的语言与行为来感动神灵,以获得神灵的保佑,实现自己的愿望。这种祈愿方式多以唱诵形式来完成,音乐感较弱,曲调平和,篇幅有长有短,以唱诵为主的祈福方式主要表现为仪式性。大多数民族都会通过歌谣唱诵的形式来祷告祈愿,主要区别在于内容不同。壮族的歌谣创作是以稻作生产为背景的,与壮族宗教文化和巫术思想有紧密的联系。广西地区的汉族群众在关于农事生产的客家歌谣《耕田佬》中也有关于牛的叙述。客家的农事歌谣不仅有非常明显的耕牛崇拜,认为耕牛在耕作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连“孩子”一词也有非常明显的壮侗语族色彩,该词除了有“孩子”之意,更可引申为“被花婆(壮族神话始祖母六甲)保佑的孩子”。虽然当地客家人是从何时开始吟唱这首歌已经无从考证,但从对牛的意象崇拜、使用壮侗语借词以及歌词整体内容来看,壮、汉群众相似的农耕方式使得彼此之间的田间劳动民俗彼此交融,从而有了非常相近的田间文化。
3.相似生产方式带来相近的民俗信仰
苗族同胞认为水牛与龙是一样的,龙可以变成牛,牛也可以变成龙。苗人对龙的认识是:龙角与水牛角相似,龙头上长着一对水牛的大弯角。牛对于苗族农人的重要性,使得苗人将牛神灵化或鬼化,因而苗人将对牛的崇拜与敬畏之情通过祭祀活动表达出来,苗族祭祀牛鬼的习俗也一直沿袭至今。唐祈等编订的《中华民族风俗辞典》中有关于苗人敬畏牛鬼的内容:“苗人病重,卜得其病为使牛鬼作祟;或中年无子,卜得为牛鬼在南门阻止女阎王送子前来,均须请苗巫来家,烧黄蜡、打锣鼓,许推牛大愿。许愿后,果然能使病转危为安,或得子,则信以为牛鬼的恩赐。”[17]从中可以看出,苗人认为不幸与牛鬼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杀牛与生育也是存在因果关系的。苗绣中也充分体现了苗人对牛所具有的崇拜之情。最初,牛对苗人农业生产耕作具有重要作用,牛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苗人对牛的感情也逐渐升华,将其神化,进而迷信它。苗绣中的牛,是具有拜物色彩的,它更多的是苗人心目中理想的形象。
壮族人认为牛是来自天上的神物,牛王诞生于四月初八,因而壮族则在每年的四月初八为牛王庆祝诞辰。在壮族大地上流传着一个关于牛王的传说,传说在很久以前,地球上寸草不生,到处黄土飞扬,岩石裸露在地表上,人们生活物资极其缺乏,苦不堪言。这一场景正好被牛魔王看到了,牛魔王顿生怜悯之心,于是就派牛王到凡间拯救苍生,牛王来到人间播种百草。牛王接受任务之时,牛魔王就提醒他要每三步就撒一把种子,但牛王记错了牛魔王给他的指示,于是他走一步就撒一把,因为种子撒得太密,草种子生长出来后变得杂乱不堪,且到处都长满了杂草,人们耕种的田地都被杂草侵占了,导致人们粮食失收。因为牛王没有按照牛魔王的命令行事,反倒加重了人们的负担,牛魔王便将牛王留在人间吃草,为农民耕田,弥补过错,以示惩罚。于是,人间就有了吃草又耕地的牛。牛的勤恳与耐劳感动了人们,获得了人们的喜爱。为表达对牛王的尊敬与感激之情,人们于是将每年四月初八定为牛魂节。而牛魔王也一直惦记着凡间的牛王,每到牛魂节这天,都会下到凡间来保佑牛王,使它不瘟死。在壮族中有这么一个传说,牛王一共有首、身、脚这三魂。牛魂会因为害怕、挨骂、过劳而导致灵魂出现疲惫、失落的状态。牛天天在野外吃草,经常受人役用,劳动非常劳累,加上经常遭受鞭打,所以它的灵魂也会失落。[18]
因而在牛魂节时,要专门给牛举行蓄魂仪式,蓄魂仪式之前要有个安栏仪式,也就是说,壮族人们会先在四月初八举行安栏仪式,蓄魂仪式则会在六月初举行,这时牛魂节才算完结。
生活在广西东部的瑶族居民,春节期间会举行舞春牛的活动。牛头用纸和竹片制作而成,涂成彩色,牛身用黑布代替,需要两个青年来扮演春牛。在表演过程中,两青年套在用纸和竹片扎成的春牛外壳里,看起来如同真的春牛。舞春牛时会有伴奏与伴舞,扮演春牛者与鼓乐队、农耕队则组成了一个舞春牛队伍,同时还有歌手一边唱诵《春牛歌》:“春牛春牛,黑耳黑头,耕地耕地,越岭越沟,四季勤劳,五谷丰登!”[19]对于瑶族人民而言,牛不仅能表达他们对已故亲人的思念之情、祈求家人团结的愿望,还寄托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富足生活的憧憬。瑶族人民对牛的崇拜与尊敬之情,以及关于牛的一系列文化祭祀活动、歌谣、舞蹈等,都构成了独特的“牛”文化。
四 近代以来的生产方式变革带来了经济互补
1.晚清的开埠通商加速了广西少数民族的农业商业化
清朝末年,清王朝宣布实行开埠通商政策,广西城市原有的闭塞状态被打破,农村与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冲击。尤其是在19世纪末,北海、龙州、梧州、南宁先后对外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到广西经商,他们将产品输往广西少数民族各个地区,再从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掠夺原材料,经济往来促使少数民族农村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城市市场需求也受到了影响。清代时期,广西位于偏远地区,工业与城市发展水平不高,商业化是推进当时广西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农产品是当时商业化的主体与核心,可以说,清代广西主要是依靠农村发展起来的,城市与少数民族农村经济互相推进,实现了共同发展。
2.晚清官方的扶持加速了广西各族的农业生产商业化
实践表明,政府是引导与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晚清时期,广西少数民族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得益于政府的支持。19世纪80年代,中国生丝出口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沿海一带城市的蚕丝生产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蚕丝需求量不断提高。面对这一形势,广西认识到了蚕丝带来的经济效益,当时任巡抚的马丕瑶便鼓励当地农民种桑养蚕,他还亲自到各州考察适合种植的地方,在各地开展种桑养蚕的宣传活动:“抵任以来,访询情形,以为劝办蚕桑可以兴利……通饬各州遍察境内何处宜桑,可以种植养蚕……下《蚕桑辑要》一册……遍查从册内所注植桑养蚕之法至周。”[20]至此,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种桑养蚕规模不断扩大,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蚕桑之利,兴转移之效速,富民之术,莫此为良。” [21]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纺织业产生与发展,国内市场对棉麻的需求数量不断增长,为规范纺织行业发展,广西地方官府结合当时情形颁布了奖励种棉事业规则,针对开垦荒地种棉、联合建立棉业会、开设棉业研究所、合资创建汽机纺纱及织布公司等有助于促进棉麻业发展的行为都给予了相应的奖赏。在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下,广西民族地区的棉麻种植规模得到了进一步扩大,为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可见,晚清时期,广西地方政府在推动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上的重要作用,是值得认可的。
3.晚清时期经济发展带来了各族思想的融合
开埠通商政策的实施,使各地经济往来联系紧密,加强了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比如闽粤地区流传的妈祖崇拜,就是由闽粤商人传人广西少数民族当中的,后来逐渐发展成各族人民的崇拜信仰。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联系、文化融合程度与思想观念上的影响程度也在不断加深,给各民族的文化意识与传统思想带来了一定的改变。
传统上,广西壮族、瑶族等民族的人们都具有严重的“轻商”观念。商业化形成之后,壮、瑶民众与外界接触越来越频繁,逐渐形成了从商意识,后来也有一些人成为商人。清代之后,壮、瑶等民族之间在实行商品交换的过程中,也会通过交流来了解各民族所拥有的先进事物,并将这些新鲜事物带回本民族来,这种交往联系不仅有利于推进各个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还进一步强化了各民族人民的商品经济观念,传统关于商人为奸、从商为贱的落后观念逐渐弱化,商人地位有所提高。
在瑶族本族当中也形成了个别专业经商活动,产生了具有农民与商人双重身份的商人与专门经商的商人,比如一些瑶族群众“最初只是兼职收购东西,后来随着收购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于是这个人就发展成了专门经营该行业的商人”。[22]
乾隆时期,浔州府地区吸引了很多粤商前来经商,粤商与当地壮人交往密切,壮人开始学习粤商的经商模式。在广西恭城河、贺江一带的瑶族聚居地,生长有大片的杉木,杉木需求量的增加,使得当地杉木出口总量不断提高。然而随着杉木收购数量的不断增加,杉木开采程度也不断提高,杉木数量已无法满足出口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居民就开始了杉木种植,瑶族村民种植的经济作物主要包括桐、茶、杉木、棕等:
有湖南省之洪江张吉昌、杨三和等以前作此黑(桐)油生意,收卖贵州桐油发财百十万两银两之富……其有桐油他省大有作用……栽桐树速成利益也……桐树最宜栽多,或五千株一丛更妙。[23]
随着近代以来国际市场对桐树、茶树需求量增加,桂北地区壮、瑶族商人多从事桐茶业采购。经营桐茶业的商人,无不走上了发达致富的道路。还有部分壮、瑶人开展手工业生产与矿业,比如在道光时期,宁明一带的壮人只会从粤商手中采购八角原料回来进行加工,咸丰年间,宁明壮人掌握了广东人的技艺,开始“蒸作茴油,贩卖得值”。[24]生产出来的产品出口到国外,获得了巨额经济利益:“近山则芋头大薯,亦宜播植。至于八角、桐油等树,更为生财大道。”[25]在与客家人的长期交流联系过程中,壮、瑶等民族之人也慢慢改变了轻商的思想。
民族经济的发展带来各民族的交流融合。清代以来,广西经济的开发程度与发展水平得到不断提高,各民族之间发展差距慢慢变小,在思想文化上的融合程度也不断加深,对各民族的民俗文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五 各民族交往合作促进了民族间和谐交融
1.以经济扎根广西,友爱睦邻
因为汉族人拥有较为先进的农业技术与手工业生产技艺,物质生活相对富足,因而很多壮、瑶等民族的人都愿意与汉族人开展经济上的往来,与汉族人合作经商,促进民族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清代以来,这种现象在壮、瑶等民族杂居的地区已经较为普遍,民族之间交往沟通越来越紧密。比如容县壮、瑶人在和汉族人开展物资往来的同时,彼此之间还会进行各种类型的经济合作,包括共同筹办造纸厂与木材加工厂、合作建设矿厂等:“康熙年间,闽客来容,始创纸篷于山中……粤人与瑶又创纸篷百余间……”[26]与此同时,还包括汉族人帮瑶民挑东西、瑶人为客家人耕田放牛等经济往来。长期的经济往来,能够有效满足各民族的经济发展需求,使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情感联系逐渐加深,为日后开展更多类型的经济合作、多方面的交往提供了条件。
2.以文化交流互融,密切关系
汉族与壮、瑶等民族长期杂居在一起,在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难免会相互融合、互相影响,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文化认同等方面,语言通用现象较为普遍,且民族之间对相互的语言都有一定的了解,能够掌握基本的使用技巧,汉族人与其他民族、其他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语言可以互通。因而,在汉族与壮、瑶等民族杂居的地区,当地人都能够通晓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这也是广西民族交往所具有的独特之处。以南宁周边的“平话人”为例:
由北方南下“流入”广西的汉人,产生民族间渐进性的民族互化过程中,在与壮族等少数民族长期共处,形成了既保留有汉族主流文化的特征,但又带有少数民族(主要是壮族)异化融合特征的“平话人文化”。[27]
比如在贵港民族杂居的地方,当地人都可以使用壮话、白话等语言,在广西很多地方也都存在这个特点。语言上的互通,为广西各民族进行更深层次的交往提供了条件。此外,通婚作为民族交流的主要方式之一,在促进民族融合团结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广西各民族杂居的地区,通婚现象也较为普遍,汉族人与苗、侗、壮、瑶等民族组成家庭,繁衍后代,民族之间建立了更为密切的交往关系。一些地方还通过通婚化解了很多问题纠纷,维护了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
各民族在生活习俗、服饰文化、房屋建筑等方面也相互影响。汉族人迁入广西之前,壮族人的房屋建筑多为干栏式结构,也就是下层饲养牛畜、上层住人,这种房屋结构是根据南方特有的地理气候特点而建的,优点是通风凉爽,然而存在卫生隐患。汉族人与其他民族生活在一起之后,汉族的建筑文化也影响了当地人,其他民族也纷纷学习汉族人的建筑形式。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互相包容、友好相处,为推进广西繁荣昌盛与文化发展提供了保障。[28]
六 结语
广西农耕文化有民族性、自主性、自足性、和谐性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由广西各世居民族经过磨合、互融形成的。这一磨合、互融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六朝之前的火耕水耨,到“俚帅”与汉族移民带来的先进中原农耕技术,再到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各族各有特点却有极大共性的农具文化、田间文化与民俗信仰,加上近代以来农业生产方式与商业发展出现变革,广西各族形成了非排他性农业经济格局,以此作为物质基础,广西各族群众在思想上实现了进一步融合。正因为这种经济联系使广西各族发展为大致相似的生计方式、文化特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才极大地缩小了各民族之间的隔膜、差异和差距,从而大大增强了广西民族团结的韧性,也为广西民族团结增添了一副稳定剂。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副研究员)
[①] 《史记》卷129《贷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第3270页。
[②]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第2839页。
[③] 陈直夫校释《万震:南州异物志辑稿》,香港陈直夫教授九秩荣庆门人祝贺委员会,第44页。
[④] 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第61一68页。
[⑤] 《南齐书》卷l4《州郡志上》,中华书局,1972.第262页。
[⑥] 《南史》卷78《夷貊传上·海南诸国》,中华书局,1975,第1951页。
[⑦] 《隋书》卷24《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第674页。
[⑧] 《隋书》卷80《列女列传·谯国夫人传》,第1800-1801页。
[⑨] 《隋书》卷80《列女列传·谯国夫人传》,第1803页。
[⑩] (宋)苏轼:《书柳子厚牛赋后》,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第2058页。
[11] 《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5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第57页。
[12] 王同惠:《广西省象县东南乡花蓝瑶社会组织》,商务印书馆,1936,第23-24页。
[13] 《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5册),第21—22页。
[14] 覃承勤、覃剑萍:《中国歌谣集成·广西卷》(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109页
[15] 覃承勤、覃剑萍:《中国歌谣集成·广西卷》(上),第112页。
[16] 金乾伟、杨树酷:《“牛魂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范式》,《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53—57页。
[17] 唐祈等主编《中华民族风俗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第74页。
[18] 岑贤安:《壮族牛魂节考察》,《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第67,70页。
[19] 刘保元:《瑶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第86页。
[20] 《关于劝办养蚕和工业问题的材料》,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第59页。
[21] 《关于劝办养蚕和工业问题的材料》,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第7页。
[22] 周光大:《瑶族解放前的社会经济形态》,《思想战线》1982年第3期,第27-32页。
[23] 《有关广西种植业问题的材料》,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第57页。
[24] 《平南县志》卷8,1835年刻本。
[25] 《思县志》卷3《食货志》,1973,第1704页。
[26] 《容县志》卷6《舆地志·物产下》,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
[27] 宋涛:《广西壮汉民族相互融合现象探析》,《桂海论丛》1999年第4期,第85-88页。
[28] 杨军:《广西多民族杂居格局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互动空间研究——广西民族区域自治60年历史经验研究系列论文之二》,《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第25·32页。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xx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xxx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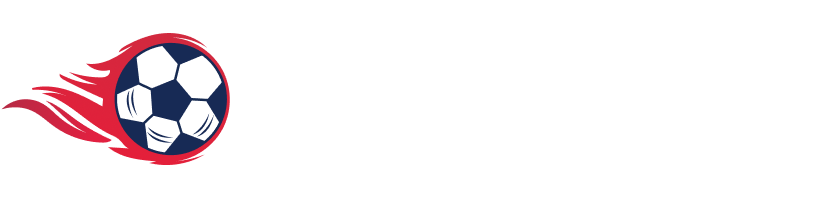





发表评论